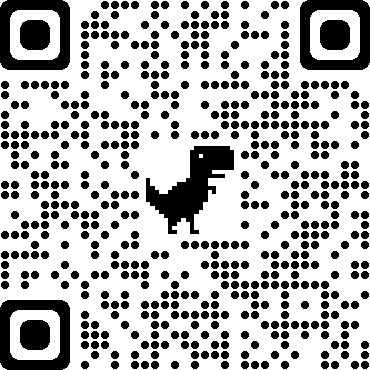一把木梳,两根断发,14岁的宁苏苏颤抖着想把散开的麻花辫重新扎紧。前一秒她还是偷吃零嘴的宁家二小姐,下一秒就被父亲亲手塞进花轿,顶替被土匪绑走的姐姐嫁给费家少爷。她不知道,这条永远梳不回去的辫子,会成为她短暂一生中被物化、践踏直至毒杀的残酷注脚。

热播剧《生万物》揭示了民国农村女性悲惨的命运:宁学祥为百亩地契卖女,费左氏为贞洁牌坊杀人,银子为三斤地瓜干爬上老财主的床。当女性的身体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时,她们的生命比田埂边的野草还要轻贱。

花轿抬进费家时,宁苏苏的绣鞋还沾着泥。父亲宁学祥骗她说“暂替姐姐几天”,实际上早已打定主意:土匪窝里过夜的绣绣已“不清白”,费家绝不可能再娶,而苏苏既已拜堂便是费家人,退回来也嫁不出去了。这个精明的地主拨着算盘冷笑:“泼出去的水,还想收回来?”仓库里堆满粮食,但他攥着地契的手青筋暴突,赎女儿要卖五百亩地,不如再“嫁”个女儿保住彩礼田。

费家的合卺酒掺了迷药。婆婆费左氏盯着苏苏喝光,转头锁死新房。醉酒的费文典将苏苏压在身下时,她还攥着半截麻花辫喊姐姐的名字。天亮后她蜷在床角,头发散乱如枯草,只会喃喃:“辫子…梳不回去了。”那截断辫被费左氏捡去供在祠堂,旁边是染血的“贞洁帕”,苏苏的少女时代被钉成费家的贞节牌坊。

费文典对苏苏的嫌弃赤裸直白。他嫌苏苏“胸脯没绣绣鼓”,更恨她毁了自己和绣绣的姻缘。圆房后他连夜逃回省城读书,三年不归。直到某天带回穿学生裙的时学娴,把休书甩在苏苏脸上:“封建婚姻害人!”苏苏捏着休书蹲在灶台边,把当年藏的花生糖一颗颗塞进嘴里,甜得发苦。
被休的苏苏成了费左氏的影子。这个守寡三十年的女人教她记账管田,却在她偷看长工洗澡时甩耳光:“寡妇门前得立座坟!”但当苏苏被地痞郭龟腰拖进高粱地时,费左氏却沉默着递来澡豆,因为郭龟腰老婆是村里泼妇,闹起来费家更丢脸。
苏苏怀孕时,银子正爬上宁学祥的床。这个二十岁的姑娘为了给母亲买药,把自己“租”给六十岁的宁老爷。一夜值三斤地瓜干,怀孕加两袋高粱。宁学祥在炕头放杆秤,完事后称粮给她:“生儿子再添半亩薄田。”银子攥着发霉的地瓜干走过宁绣晒的破屋,听见里面传来婴啼,绣绣早产的儿子刚咽气,她丈夫封大脚为抢回被踩进泥里的死婴,正和催租的长工厮打。
郭龟腰在苏苏临盆那晚踹开费家大门。他满身酒气嚷着要摸儿子,却把费左氏逼到墙角撕扯衣襟。三天后,费左氏熬了一锅红豆粥。苏苏喝第二碗时嘴角溢血,郭龟腰抽搐着栽进粥盆。费左氏整理好寿衣,仰头灌下毒粥。三具尸体旁,新生儿的啼哭刺破黄昏。
宁学祥的死与银子无关。土改时佃户举着锄头冲进宁家,他疯狂吞咽地契纸,喉管却被铁头的镰刀割开。血漫过祠堂供奉的“土地神”牌位,银子抱着儿子冷眼旁观,她终于不用再为地瓜干上床了。
费文典在城里报纸上读到苏苏的死讯。他扶了扶金丝眼镜,对怀孕的时学娴笑说:“旧式妇女,终究跟不上新时代。”窗外飘着解放区的传单,印着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。宁绣绣在母亲坟前烧了双红鞋。那是苏苏七岁时羡慕姐姐的嫁鞋,她偷攒三年绣花钱才买到。火苗卷过鞋面珍珠时,封大脚往灰烬里撒了把新麦:“苏苏爱吃麦芽糖。”远处,银子的儿子追着合作社的拖拉机奔跑,裤袋鼓鼓囊囊,里面塞着宁学祥咽下的半张地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