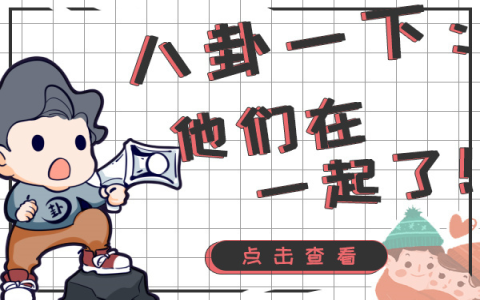那个在FIRST青年电影展提问时频频被主持人打断的女孩,此刻坐在镜头前像在谈论别人的故事。“它已经翻篇了,”张一卿——更多人叫她“185同学”——如此定义这场风暴。她甚至为那位主持人解释:“我的提问经验不足,为了让它不这么尖锐,导致我的措辞比较长,再加上当时已经很晚,我是最后一位提问者,我不觉得她是在针对我。”这个被贴上“勇猛”标签的女孩,第一反应是保护对方:“我不希望具体的人因为我受到伤害,因为我也被网暴过。”

张子卿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提问。
而面对主持人对她“冲冲的”评价,她认为“这是种赞誉”。张一卿在镜头前笑得坦荡,“我人生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冲劲儿带给我的”。当全网为这场“打断提问”的风暴争吵时,风暴中心的女孩早已抽身离去。这份超越年龄的清醒,源自一场持续25年的生存实验——她的人生,本就是与规则对抗的即兴创作。
冲劲的源头:在边缘地带野蛮生长
张一卿的人生仿佛一场跌宕起伏的戏剧。“我好像从没被任何群体完全接纳过,”她回忆道,“但幸运的是,我的父母给了我极大的自由。”
这份自由,让她在普通孩子都在为升学苦恼的时候,敢于拿着租借的摄像机搜集全班早恋故事拍成微电影。为了剪辑影片,让爸爸找理由给她请假,到最后老师都不再回复消息。
最后,这部名为《你是年少的欢喜》的微电影在学校的报告厅放映。报告厅里挤满300多人,还有人是站着看完的。
短片控诉:“提高一分,只能战胜166个人。这166个人,是1990千米的距离,是1000块钱的机票,3小时的飞行时间,4年的思念,和一辈子的遗憾。”很难想象当时的老师看完是什么样的表情。

《你是年少的欢喜》截图。
但能确定的是,这部生涩的处女作让她打开了影视的大门,让她体味到了创作的快乐。于是,在高三那年,她选择了艺考,目标是导演系,剑指“四大院”(北京电影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、中国传媒大学、上海戏剧学院)。
套用当时的流行语: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张一卿一心想从艺,艺却没那么简单。第一次艺考,落榜;第二次艺考,落榜;第三次艺考,离过线差了三道选择题,还是落榜。
她心灰意冷地将大学志愿全权交给了父亲填报,命运给出了它既定的答案:西安外国语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,“这是我三次高考都能考上的大学”。
换句话来说,三年来的努力仿佛毫无意义。
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,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“我想去西藏,站在雪山脚底下哭。”但妈妈回复她,爸爸创业失败,家里没钱。
自由再次给了她勇气,这一次,她攥着她的全部家当——1685元现金,20岁孤身一人就踏上了开往西藏的绿皮火车。硬座车厢冷得像冰窟,她一夜冻醒三次,却在本能翻找厚外套和不破洞的牛仔裤时突然觉醒:原来那个不想活了的自己其实不想被冻死,也从没想到自己其实这么有劲。

穷游西藏的张一卿不舍得花3块钱买水,但是转头买了青稞酒。
在西藏的那段时间,她用青旅义工身份换取生存,把舍不得买水的3块钱换成街头青稞酒,在色拉寺峭壁上滑滑梯。这一系列名为《拿一千块在西藏穷开心》的游记让她在B站收获了超过10万的粉丝。
评论区里有人分享自己的痛苦,有人忙着抚慰这些受伤的人,陌生人之间在此交换勇气。“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存在还会有一些意义。”
领奖台上的困惑:当野路子撞碎学院高墙
张一卿的视频没有精美的画面,都是一帧帧她随手记录下的生活画面:有的人脸只在一个角落,有的持续好几秒都在晃动,有时手机干脆就飞出去了,看起来有种漫不经心的感觉,也让她的视频在一众愈加精美的画面里看起来特立独行。
“不是我坚持要拿手机拍摄,只是我太懒了,”谈到这里她弯着眼睛笑起来,“第二个可能是当你拿相机的时候,这个世界会觉得你要干点什么,所有的东西就没那么自然了。”
她在自己的作品里,一直坚持着一些宝贵的东西,比如只在那一刹那的真心。“我很喜欢这种真实的感觉。”
凭借着这份不加雕琢的、近乎本能的“真实”,2021年她站上了第十五届FIRST青年电影展领奖台。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谢飞点评:这个女孩子的短片,做得很精彩,很真切。

《嘣》获得第十五届FIRST影展超短片单元人气短片奖。
这部名为《嘣》的获奖短片跳脱出了传统的叙事,没有基本的“故事三要素”。有的只是她裹在旅馆的一床白色被子里,凌乱的头发就像她理不清的少女心事一般,半梦半醒间的眼神,天马行空的3分08秒。
然而,手握奖杯的张一卿,感受到的并非全是喜悦,她陷入了长达两年的自我否认:“我甚至觉得玷污了电影节水平。”
时间是最好的解药,也是最重要的审视者。两年后,当风暴平息,尘埃落定,她再回首看那个站在领奖台上局促不安的自己,终于能给出一个更加笃定,也更为和解的答案:“总要有一个片子获奖的,那我的片子可以获奖一定有它的原因。”
她开始理解《嘣》的价值,恰恰在于它打破了某种预设的“标准”。它不符合主流对“电影感”的传统期待,但它用最直接、最私人的方式触碰到了人心的共通之处,这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创新,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野性力量。
幸福主义宣言:在风暴眼里修自己的路
这份与自己创作基因的“和解”,成为了她下一段旅程的心理基石。带着对“真实”更深的体悟和对“创新”边界的探索欲,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:远赴重洋,去看更广阔的世界。赴美的费用,正是她这几年坚持用手机记录生活、在B站野蛮生长所积累的成果——80万粉丝的陪伴与认可,最终化作了一张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门票。
与最初大多数希望她“一切顺利”的声音不同,留学的一年间,她遭遇了最大规模的网暴。
因为不爱做前调,她的帆布鞋反复被雪浸湿、信用卡被冻结、迷路到坐警车……每次更新的视频下面,都会有人评论她“卖惨”“活该”“愚蠢”“矫情”。
她在质疑声中崩溃,又只能接着跌跌撞撞去迎接生活给她的考验。“当时不理解,作为一个长相平平、学历平平、家庭平平,只是有点小运气的普通女孩,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指摘和关注。”
一直作为边缘人物的成长经历,没有让她沉浸在崩溃里太久,她在视频里平静地说:“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。”
两年后再回望当时的自己,她总结为没有自知之明。“在一个公众平台进行表达,被大家评论好与不好都是他们表达的权利和自由。别人可以伤害到你的权利是你给别人的,而我能做的不是让他们闭嘴,而是不把伤害的权利给他们。”
此后,她一直贯彻着这条准则,将“我”作为人生的一切前置。“有些话我一定要讲,有些东西我一定要让它存在,有些表达我一定要被人听到,我觉得我有一种使命,有些故事它找到了我,我只是一个载体,这个东西从我这里流出去。”
被问及人生目标,这个曾把“成为厉害的导演,拍一部厉害的片子”作为目标的女孩给出了意外答案:“我要成为幸福的人。”
五年前的野心悄然溶解。“电影只是我幸福拼图的一块,如果哪天没有表达欲了,我就去开采耳店,虽然朋友不信任我掏耳朵的技术。”她笑着补充,“但给人掏耳朵也能很快乐。”
这也是她对自己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提出问题的回答:没有创作欲,那就不做了。
采写:南都N视频记者 鹿筱悦